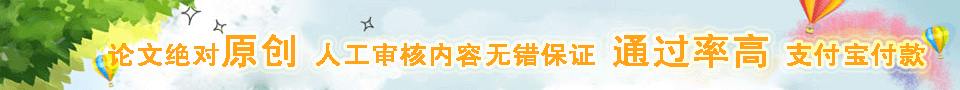(一)研究缘起 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胜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我们总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不希望受到干涉。对于儿童则不然。在我们的印象中,儿童就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在中国,孩子在家中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一旦他们有不符合期待的行为出现,便会受到严厉的斥责,直至他们做回“乖宝宝”为止。为什么儿童近乎无自由可言?为什么成人剥夺儿童的自由正如维护自己的自由一般理直气壮?儿童对此又有何看法?我想一探究竟。 (二)文献综述 从自由被剥夺的程度看,儿童并不比奴隶好到哪里去,而这似乎早已成为一种约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将自由与儿童联系在一起都会引人发笑。想搞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对自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还有一点不能遗忘,那便是自由的危险。 1.哲学中的自由概念 自由有两个层次,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这两层意义虽然不同,但仍然密切相关。 (1)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伯林“两种自由”的理论如此著名,以至于成为当代关于自由的研究的一个基本场面。 “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但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我既不想讨论这个变化多端的词的历史,也不想讨论观念史家记录的有关这个词的两百多种定义。我只想考察这些含义中的两种,却是核心的两种;我敢说,在这两种含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我敢说,仍将会有丰富的人类历史。freedom 或 liberty(我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 词)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遵从许多先例)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 (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这两个问题是明显不同的,尽管对它们的回答有可能是重叠的。”1 对应这两种自由概念,伯林也指出,“两种概念的每一种都有堕落为它被创造出来要去抵抗的那些恶的倾向”。2 一个人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因为否则,那将是一个所有人可以没有限制地干涉所有人的状态;而这样一种‘自然的’自由将导致身处其中的人连最低需要也无法获得满足的社会混乱;要么,弱者的自由将被强者所压制”。3“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4“一些人的自由必须依赖于对另一些人的限制。”5 另一方面,“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中,而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或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划定私人生活的领域与公共权威的领域间的界线。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里,是一个有争议甚至是讨价还价的问题。人大体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一个人的活动是完全私人性的,是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闯入别人领地的。”6 相比之下,“积极”自由的偏离更需引起关注。“如果我们考虑自我导向,亦即受某人的‘真正’自我的指导的欲望,在历史上所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在两种自我之间做出区分的后果将会变得更加清楚。一种是为了获得独立而采取的自我克制的态度,另一种是为了完全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自我实现或完全认同于某个特定原则或理想的态度。”7 卢梭说,“人只要求他能够实现的,也只做他所要求的。这就是真正的自由。”8“当外在世界证明是特别地沉闷、残酷而又不公时,逃至真实自我的内在城堡这样一种理性圣人的概念便以个人主义的形式兴起了。”9“在一个寻求幸福、公正或自由的人觉得无能为力的世界上,他发现太多的行动道路都被堵塞了,退回到自身便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10伯林对这种定义以及整个这种思想路线提出了批评。 还有一种情况,“开始时作为自由学说的东西结果成了权威的学说,常常成为压迫的学说,成为专制主义的有益武器,这是一个在我们时代变得太熟悉的现象。”11其基本假定如下:“首先,所有人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真正目的,也就是理性的自我导向的目的;第二,所有理性存在者的目的必然组成一个单一、普遍而和谐的模式,对于这种模式,有的人比其他人更能清楚地领会到;第三,所有的冲突,因此所有的悲剧,都源于理性与非理性或不充分理性——生活中的不成熟与未发展的成分,不管是个体的还是共同体的——之间的冲撞,而这种冲撞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在完全理性 的存在者那里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当所有人都被造就成理性的时候,他们将服从出自他们自身本性的理性规律(这些本性在所有人中都是同一和一致的),因此成为完全服从法律且完全自由的人。”12为了使人变得理性,教育应运而生。教育,费希特说,必然以这种方式进行:“你以后肯定会认识到我现在这样做的理由。”13“不能希望孩子理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被强迫送到学校;无知者——一定时期内的人类大多数——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服从那些不久将会使他们变得理性的法律。”14“强迫也是一种教育。”15“你习得了服从超人的伟大美德。如果你无法理解你的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利益,就不能指望我在使你变得理性的过程中与你协商或遵从你的意愿。结果,我不得不强迫你注射天花疫苗,即使你可能并不愿意如此。甚至穆勒也会说,在没有时间去警告他的时候,我可以用强力阻止一个人跨上一座快要倒塌的桥,因为我知道,或者有理由假定,他不太可能想掉进水里。”16“为了在未来能增长见识,教育使强迫变得合理。”17 伯林在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基础上,强调了保护消极自由的重要性。“通常,强调消极自由,是为了给个人或群体多一些路径;强调积极自由,通常开放的路径较少,但对于沿着它们前行却有更好的理由或更大的资源;这两者可能冲突也可能不冲突。”18 (2)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 除了《自由论》,柏林还有一本《浪漫主义的根源》,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哲学上自由观念的演变。书中提及三位德国思想家,伯林称他们为“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康德对意志的至高无上性给予了肯定。“人之所以为人,在康德看来,只因为他能够做出选择。人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动物、无生命的物体、植物——之间的区别在于人之外的事物受制于因果关系,人之外的事物必须严格遵守一些预设好的因果程序;而人却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这个,意志,便是区分自然界中人与其他事物的东西。意志就是能使人们选择善或恶,正义或非正义的东西。除非同时也可以选择非正义,否则,选择正义本身并不是多大的功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些执意终身选择真善美的人们不能因此自诩为有功之人,因为不管这种选择会产生多么高尚的结果,行为本身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康德推想,道德功劳的观念,道德应得的观念,哪些该得到我们的赞扬,哪些该受到我们的谴责,哪些行为方式该受到鼓励或指责,所有这些都基于这个前提:即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出于这个原因,家长式专制主义,至少是政治意义上的家长式专制主义,成为他强烈憎厌的东西之一。”19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自由是一种信仰,一种公设。人有自由,又是人有道德义务和责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谈不上道德。“如果价值外在于己身,如果外界强力迫使我们行动,那么我们就会沦为它们的奴隶——也许那是一种极其崇高的奴役方式,但奴役就是奴役。要想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就应当自由自在地信奉某种道德价值。你或许可以信奉某种价值,或许不,但自由就在信奉之中,而不在价值本身的地位、合理性或其他方面,在于你信奉或不信奉,在于你无须别人要求自己就能信奉。至于你信奉的是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也许它是经由理性方式获得的,不过,独有信奉或不信奉本身对你才有价值。换句话说,称一种行为是善还是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实就是说存在着自己可以自由决定的信奉行为——这种行为后来被称做担当行为、奉献行为或切身行为——就人而言。”20 “席勒拒绝了康德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康德所说的意志可以把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但把我们送上了一条狭窄的道德之路,送进了一个太刻板、太逼仄的加尔文世界,在那里,人们要么沦为自然的玩物,要么谨守路德教那套严格的职责(康德一度认为那套职责会戕害和毁灭、扭伤和扭曲人的天性)。如果人想要获得自由,他不应该只有履行职责的自由,他还必须拥有选择遵循自然或自由地履行职责的自由。他必须居于主动位置,或选择职责,或选择自然。”21 “第三个思想家,我要捎带提一下。他就是费希特,一个哲学家,康德的信徒,他也给自由的观念补充了一个激情洋溢的解释,下面这段典型性的引言可以说明这点:‘只要提到自由二字’,费希特说,‘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而一旦说到必然性这个词,我的心就开始痛苦地痉挛。’” 22“自由是行动,而非冥想。‘自由本身算不上什么,’费希特说,‘变得自由才是向天堂的飞升。’ 我建造我的世界正像我创作我的诗歌。”23“费希特从个人说起,他自问什么是个人,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只要人还是一个空间三维体,他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自然会以千万种手段限制他。因此,唯一能够达到完全自由的是某种大于人本身的东西,某种内在的东西——即便我无法控制我的身体,我仍可以控制我的精神。”24“自由是免于障碍的自由,自由是制造自由的自由,自由意味着你在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时免受任何事物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