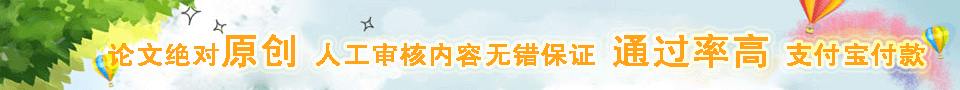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少翻译家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标准,有的人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而有的人则提出“硬译”标准。本人认为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一成不变地进行翻译是产生不了应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进行调整,在保持“神韵”的准则下语言上作些变通,这便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2]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不同于翻译其他科技类,政治类和新闻类的文章,文学是带有深深文化烙印的,是创作者精神追求和情感的集中体现,这也是翻译成目标语中最难以传达给读者的。所以以下主要是本人在此次翻译《瓦尔登湖》第二章节选的过程中一些切身体会: 第一、透彻地了解翻译材料。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原文并没有任何陌生的单词或者复杂的句子,但是却无从下手。例如,《瓦尔登湖》原文中关于作者梭罗对农场美景的态度“I am monarch of all I survey,My right there is none to dispute.”,这句话中的“survey”一词,通常翻译为勘测,勘察,作动词用,但是从原文的语境来看,梭罗所表达的意思并非如此,而是对于农场的美景,他就像是一个国王一样,谁也不能质疑他纵览美丽风光的权利,所以“survey”因根据具体语境,译为“纵览,眺望”的意思。因此在做翻译实践时,要避免眼高手低的情况,表面上看原文,似乎大概明白其中的意思,然而翻译并不等于概括段落大意,是要字字较真的“ 苦差事”。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作者要表达的话语一字不缺地传达给读者。另外,英语的许多习惯用语和俚语是不能够望文生义的,否则会导致对原文的扭曲。 第二、翻译重在实践与积累。所谓熟能生巧,古人所说的确实有其道理,翻译虽然是要求译者具备一名“杂家”的条件,但是它与其他技艺没什么区别,翻译者之所以对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如此地得心应手,主要是他们平常注意对各种固定翻译的积累与总结,在这次翻译《瓦尔登湖》中,最为深刻的是作者梭罗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作品中多次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譬如,在描写蔚蓝色的山脉时,用的是“......I could catch a glimpse of some of the peaks of the still bluer and more distant mountain ranges in the north-west, those true-blue coins from heaven's own mint ......”,句中“coins”表示钱币,铸币。“mint”则是铸币厂的意思,生产铸币的地方,毫无疑问,当然只有铸币厂,也只有铸币厂生产出来的才是铸币,用这两者的关系来暗指山脉的蔚蓝色只能属于天空的,是纯自然的颜色,充分地体现了一语双关的特色。又例如在翻译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演讲稿之前,译者通常会花功夫去研究和收集这位领导人的语言风格,有的领导人说话喜欢引用古诗词;有的领导人说话婉转含蓄等等,这些都是靠积累与实践来实现的。 第三、意译与直译。意译法是直译的升华与提炼,特别在散文与诗歌的翻译中,意译法尤其重要,因为散文讲究“神”,诗歌讲究意境,两者都是抽象的概念,如何把它们更好的呈现出来,需要译者的润色。在选文中,杨先生译本语言更为优美和细腻,仿佛是他本人在写的一部散文集,而徐迟先生的译本更多是采用直译法,虽然他在语序的调整上花了心思,可是缺少了一点散文该有的韵味。当然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于原著”,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翻译的“再创作”,正如1978年,许渊冲在“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一文中也谈到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说:“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无论是意译,还是直译,只要尽可能地贴近原著,并且将原语转化为更容易理解和把握的目标语,那么翻译的作用就体现了。 第四、理解与词义的选择。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反复推敲,深入分析,才能对词义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翻译时切忌望文生义,甚至不顾上下文的联系,拿一个词的常用的词义来生搬硬套,特别是这一篇选文的作者是善于遣词的梭罗。 第五、造句。翻译中的不仅遣词难,而且造句也不是易事,特别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翻译技巧的研究鲜为人知,这样必将造成文不达意。“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难存原文,只好就径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1998:2),关于这一点,本人颇有体会,选材来自于19世纪美国的自然主义时期的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距离我们已经有上两百多年之遥,并且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形成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差异,这样倘若是译本过于拘泥,死守原著的言语和词句,往往会使读者失去兴趣和耐性,在这次的翻译中,本人也陷入了死守原文的困境中,导致译文的翻译腔调过于明显,没有从读者角度出发,如“Moral reform is the effort to throw off sleep”,在没有进行修改之前,我译为“修身养性是为了摒弃睡意而做出的努力”,这样似乎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汉语中,动词比名词更有感染力,因此必须以为“修身养性是为了努力摒弃睡意”,才能贴近目标语,靠近读者的表达习惯。此外,在翻译实践中的“假朋友”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为了面向群体的不同,要尽量考虑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 第六、归化。引用钱钟书先生所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了‘化境’”。 若译文能与原作形神兼似,又自然浑成,无雕凿痕迹,也就达到了“化境的”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选择与原著正确对等的词,更要体现原著的风格,达意传神,才能表达原著的思想与神韵再现。这次的翻译选取了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尽管是完成了翻译的任务,但始终未能达到“归化”,从译文来看,许多地方都带有自己的表达习惯和方言的踪迹,因此,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神韵的再现,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