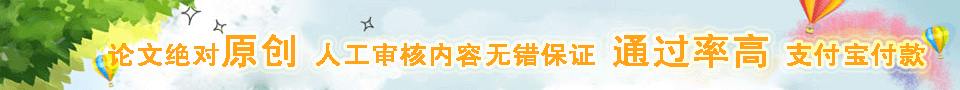《妄稽》虽未整理完全,但还是可以一窥梗概:大致讲述的是西汉妒妇“妄稽”的故事,地点在荥阳,围绕一位名族士人“周春”和他奇丑无比的妻子“妄稽”以及美妾“虞士”之间的家庭恩怨展开。显然可见这是一篇以家庭婚恋为题材的叙事赋。 自古以来,通过以家庭婚姻问题为素材展现现实生活、表现重大社会文化内容的文学创作屡见不鲜。神话传说暂且不论,《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家庭婚姻题材的作品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周南•关雎》作为《诗经》第一篇就以情诗开篇,描写一位懵懂贵族青年对于窈窕淑女的思慕之情,写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千古不变的真理与自然法则,其感情十分纯朴而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①” 《诗经》中除了写小儿女的情感还有一些反映婚姻和婚后家庭生活的诗,虽然较情感诗而言不够丰富,却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如《周南•桃夭》一诗,开篇写桃枝之柔嫩、鲜花之娇艳,实际是为了衬托新妇的年轻娇媚,并对她出嫁后与夫家处理好关系予以美好的祝愿;再如《郑风•女曰鸡鸣》一诗,写夫妻之间幸福美满的生活,作者也表达了希望他们永远和乐的祝愿。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家庭婚恋题材在各个时期,各类体裁的作品中皆有体现,如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以及诗歌中大量的闺怨诗等等。而挖掘这些家庭婚恋题材作品的背后,无一例外的体现了某一时期的家庭伦理观念,显然这与植根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戚戚相关,着重表现为礼乐教化对家庭伦理的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极为值得探讨的就是礼乐教化影响下的女性意识的发展。 女性意识就是指与女性相关的思想观念,它可以说是历史的产物。女性是什么?代表什么?似乎难可一概而论,大致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观念约束着女性的思想观念,而不同的女性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一般状态。中国两千多年来不断传承的女性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与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戚戚相关,深受封建制度、宗法社会以及礼乐教化的影响。从远古到《妄稽》存在的上古,女性意识的发展基本经历了从原始化走上封建化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女性是尊崇膜拜的对象。在神话中,论女性中地位之尊贵显赫,恐怕没有比得上西王母的了。传说中的西王母乃是西华至妙之气孕化出的女神,是掌管天界众女仙名籍的首长,是美好、贤淑、奉献、仁慈博爱、睿智的化身。“女神的核心价值在于是一个自足的崇高生命创造者形象,并由此向繁荣女神、丰收女神、爱神方向衍化②”。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经济基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层建筑,原始社会的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可以概括为生产力极其低下、自然条件极其险恶,对他们来说维持生命和繁衍无疑是最直接和迫切的需要。再者,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处于蒙昧状态,仅仅是依赖于自然,还无法理解人类本身,对家庭、伦理更无深刻概念。因而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体现的基本是对女性的崇拜与敬畏。 这种现象到了先秦则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源于礼乐教化的形成发展。《诗经》中大多诗篇的创作集中体现出原始的女性观念日渐消退,新的女性意识开始构建即封建化的女性意识。《诗经》中作品的创作时期基本在周代,周礼从繁荣昌盛到礼崩乐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了无所不在的制约作用。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乐,成于礼①”他把《诗》、礼、乐三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强调他们之间存在的内部关系。《诗经》中的每一次情感的流露都伴随着道德教化,其中体现的女性意识已经明显不同于原始社会的女性意识,称其为“事父”、“事君”的教科书亦不为过。但《诗经》中依然遗留有不少受原始女性意识影响的作品:如《鄘风·柏舟》,女子为了嫁给自己心爱的男子,甚至不惜违抗父母之命;又如《郑风·将仲子》,一女子做出艰难抉择,泪别爱人,但她对仲的思念情深,是“礼”无法磨灭的。因此总体看来,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时期的女性意识有一定的受伦理教化影响的倾向,女性地位也大不如前,但仍处于原始女性观念向封建女性意识转变的过渡期。 到汉以后,这种封建化女性观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以《妄稽》与基本同时期的《孔雀东南飞》为例。这两部作品都是以家庭婚恋为题材的代表,但与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主要写情感和婚姻状况不同,这两部作品通篇都在围绕女主人翁进行叙说,着重刻画女性人物形象,不难看出是在突出女性。并且这两部作品都着重凸显了女性的强势一面。例如在《妄稽》篇中,面对丈夫周春对自己不满,想要纳妾的情况,妄稽不仅不伤心退缩,反而强势的阻拦周春买妾,对丈夫大怒,斥责他“错我美彼”,甚至和公婆大声辩驳。不仅如此,她还坚定自己的主母地位,对小妾大打出手,甚至百般折磨——“柘修百束,竹笞九秉。昏笞虞士,至旦不已。①”对此,丈夫周春尽管毫无尊严却没有改变的能力。妄稽进一步恐吓周春将小妾卖掉,否则诉诸官司,(“速鬻虞士,毋羁狱讼”②)真可谓凶悍无比。从文本来看,妄稽虽为女性,在家却尽显强势,拥有很高的家庭地位。在《孔雀东南飞》中,刘氏虽然相貌温柔,实则外柔内刚,面对自己的悲惨处境,从开始便直言“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不愿屈就公婆。刘氏在再嫁前见到焦仲卿之后,相约“黄泉下相见”③便毅然“举身赴清池”以示守诺不负,决断刚烈,一至如此。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它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似乎以往学者的讨论总摆脱不了爱情和反对封建礼教这两个结论。而事实上爱情拗不过现实,封建礼教也不是当时女性可以成功反抗的。 首先,刘兰芝的刚烈决断也不能改变她悲惨的命运。她从小就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④她勤劳贤惠,与焦仲卿成婚后,本该生活幸福美满,可是身为女子,幸福不能把握在自己手中。她的婆婆以“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⑤”为由将刘兰芝赶走。回到娘家后,她的婚姻更没有了自由,其兄因钱财地位,一手操纵强行将刘兰芝再嫁。究其悲剧原由,正是封建与宗法的严苛与非人性化让刘兰芝一步步走向毁灭。 再看《妄稽》,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既表现出妻妾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又打破常规,凸显了妄稽的女性地位,妄稽与丈夫、与公婆之间的关系又悖于封建等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封建礼教的主旨是成立的。这篇文章与《孔雀东南飞》一样,上演着一部家庭悲剧,作者告诉我们其原由乃妇人之妒——“我妒也,不知天命乎!祸生乎妒之。①” 但倘若我们追溯下去,妇人之妒因何产生?无疑是丈夫对美色的追求所致。既如此,作为丈夫的周春,是否应该对这样的家庭悲剧做出反省呢?但事实上这一情节在文中并没有出现。因此不得不思考,或许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丈夫对美色的追求并不是对妻子的背叛而是一种理所当然,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使然,无论妄稽如何的蛮横骄纵,也终究无法阻止丈夫周春再纳妾。由此看来,《妄稽》中所体现的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或者说依然是失败的。 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集大成。这一时期以阴阳五行来理解家庭,所谓“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家庭由夫、妻二者组合而成,因此重视家庭问题,不得不加深对女子作用的认识。在董仲舒所提出的家庭观中,虽然承认了女子对家庭、对国家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作用,但更强调的是“阳尊阴卑”,将女子放在从属地位,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对此都有体现,如张衡的《同声歌》一文中,尽写新妇向其夫列许自己将如何恪尽妇职,完全默认了自己难以自主自立的从属地位。可见汉时女子完全受礼教压迫,不能自主。从这样的现实背景看来,赋中的故事不见得是真实的,应该说很可能是作者杜撰的,因为作者极夸张的表现了妄稽的丑与恶,并且结合当时社会,周春作为一个氏族子弟,怎么会被自己的恶妻欺压得毫无出头之日。因而我认为,《妄稽》中所叙述的故事,事实上只是反映了女性战胜封建礼教压迫的强烈愿望。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无奈与残酷,只有在虚构的世界里才能寻找一丝安慰与解脱。这样的虚构更揭示出现实中女性命运的在劫难逃。《妄稽》作为罕见俗赋,更加作证了汉以后女性地位的底下以及女性意识封建化的彻底转变。 《妄稽》创作的时代,如上文所述,处于汉武帝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汉赋产生、兴盛的时期,许多名赋被记载于《史记》这样的史学巨著中流传至今,比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等。且其华丽、绝妙之辞藻,高雅之格调,深邃之意旨,越世之高谈,都为后世骈文之榜样。《妄稽》与传统文人赋为代表的汉大赋不同,内容贴切民间故事,语言平实,属于文学史意义上典型的“俗赋”。这类赋文虽然为民间百信喜闻乐见,但士人却不看重,不能被载入册籍,因而流传甚少。但是也正因为其内容贴切俗世,详细记载了当时百姓的实际生活,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而凸显出极为重要的价值,成为研究古代家庭婚姻以及女性意识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