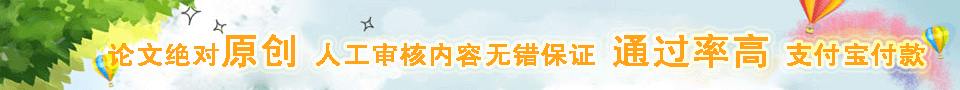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苹果树》的故事背景能够在《人生》中找到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在两个爱情故事的发展中,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悲剧的助推者。 (一)主人公对身份、地位的态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已经走过了黄金时代,社会固有矛盾开始逐渐尖锐化,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且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变,阶级意识依然根深蒂固。《苹果树》中的艾舍斯特出身于资产阶级,这样的环境在赋予并逐步深化他的阶级观念,影响着他的选择。因此在车站时,他头脑中一直占据上风的想法是:“我宁愿毁掉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啊!那样做就意味着放弃他所尊敬的一切,放弃自己的自尊心。”[3]P278 归根结底,他要做的并不是选择单纯还是成熟、有才华还是没才华的那一个。而是要决定顺从、尊重社会惯例,过中产阶级的生活,还是违背“社会常识”、“挑战”世俗,遭受别人的嘲笑。即使他没有遇到哈利德一家人,他最后也不太可能会把梅根接进城和自己一起生活。 与艾舍斯特相比,高加林的处境可谓艰难而尴尬。艾舍斯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男性,在爱情关系、社会身份上,都是绝对的强者。而高加林则不同;他是男性,在与巧珍的爱情关系中居于优势;但是,“乡下人”的身份如影随形,他“城里人”的幸福如沙上之塔,转眼成空。 高加林所处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新旧更迭的时代。对于他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大量新鲜事物的涌入令他们的内心躁动不已。在县城读高中的高加林爱读书看报,也曾有过高远的梦想:“他很关心国际问题,曾梦想过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3]P36 但高考一旦落榜,在当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高加林就“跌落凡尘”,很难再有别的出路。热切的愿望,逼仄的现实,高加林的上进心在时代的催化下变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只有在城市里才能取得成功,才能成就自我,否则便辜负了自己的才华;在他的 “人生字典”里,城市就是成功,而乡村就是失败。就是在这样的偏执观念之下,高加林一步步迷失了自我,丢掉了那“金子般”的巧珍。 艾舍斯特和高加林在面临爱情的抉择时,都选择了城市女性。前者是想继续保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后者是想去获得这种地位。虽然二人的起点不同,处境各异,但其选择的归结点是相同的——身份、地位,终究重于信诺与爱情。 (二)乡村的妥协,或宽容 在《苹果树》中,梅根面对艾舍斯特的抛弃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她之所以这样做,和她农民阶级/女性的双重自卑心理是分不开的。梅根本不敢奢望与艾舍斯特结合,但艾舍斯特却给了她希望与承诺,转眼间又“人间蒸发”,这给梅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再加上梅根太过单纯、软弱,在这一段本就不平等的爱情中一直选择妥协和顺从,最终应验了自己之前说过的:“如果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会死的。”[2]P257 这种妥协是以梅根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女性对社会的妥协:面对不公的待遇,她们选择独自承受伤害和痛苦,甚至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痛苦。这也是乡村对城市、“下等人”对“上等人”做出的无奈妥协:城市可以依靠自身的绝对优势掌控乡村;反过来,乡村对于这种掌控却无法反抗。 《苹果树》中的乡村是牺牲品,顺从城市,被城市所“消费”;相比之下,《人生》中的乡村对城市的态度更为复杂,不同的人物身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的是屈服、妥协,有的则是宽容。 高加林接受了“关系为王”的规则、一心“往上爬”,割断了与乡土的情感纽带,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屈服与妥协。从一开始希望用个人奋斗争取更好的工作,到教师职位被顶替。这一时期的高加林对于高明楼、马占胜之流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他是“关系”的直接受害者。后来,高加林的叔父成为劳动局长,马占胜一手包办,安排高加林到县城工作。 对这一切,高加林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他亲眼见证了“关系”的强大威力,而且自己是利益获得者。此时的他早已丢掉了“写状子告他们”的个人立场,也丢掉了那种以踏实奋斗的自尊。 以高玉德为代表的部分村民向权力“低头”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高玉德一生都是与黄土地打交道,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他和身边的人自然都有属于他们的一套处世之道。当高加林要写状子告发高明楼、马占胜时,高玉德便本能地去阻止儿子做“傻事”。 “人家通着天哩!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3]P11按照高玉德的理解,高明楼他们能做这些事,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是一种“正常现象”。反过来,自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毫无权势,即使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己身份比人家低,也不应该去妄加指责。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的生存模式是单一的,在贫乏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养成了极强的忍耐力与顺从的习惯,甚至信奉传统的“宿命论”:他们认为什么人吃什么饭,做什么事都是注定的,不要不自量力地“挑战”处在高位的人。也可以说,许多农民对于权势心存畏惧,这种畏惧心理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向化身权势的城市做出妥协也是无奈之举。 然而,高加林由城市再次回到乡村,从中可以看出路遥对于那个时代的理解:城乡二元体制固然有不合理的一面,但就总体来说,整个社会体制的运作是有序的,透明的,实现了相对的公平。虽然高加林之前坚决地背弃了乡村,但乡村还是以宽容之心再次接纳了他——不管你曾经是多么地鄙弃乡村的落后,当你遭受挫折时,那片土地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不仅如此,“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3]P248 就像高明楼曾经说过的:“别看你我人称‘大能人’、‘二能人’,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3]P94 只要高加林愿意把心静下来,愿意把乡村看作施展才华的平台,是可以在乡村做出一番成就的。 |